2011-01期●人物●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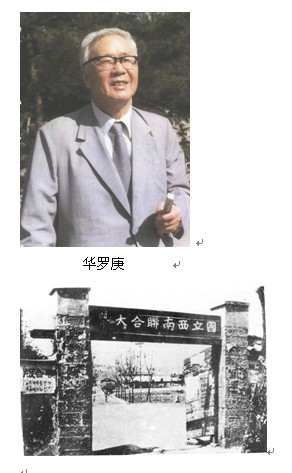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诞生于苏南金坛的一个贫民家庭。他刻苦自励,精勤不倦,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三所大学组成联大以后,他们共同招生,各自延聘教授,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们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维护优良的教学风气,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
此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的华罗庚忧心如焚。1938年初秋,他放弃了苏联科学院的访问邀请和逗留国外的计划,回到祖国抗战的大后方云南昆明,与同胞共赴国难。
华罗庚到达昆明后,不少大学竞相争聘。清华大学教授聘任委员会开会研究讨论时,著名物理学家、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将华罗庚在国内外发表的数十篇数学论文拿出请委员们评审,竟然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读懂。鉴于华罗庚的学术水平和卓越才华,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提出让华罗庚越过讲师和副教授,直接破格担任数学系教授的动议,最后表决一致通过。华罗庚用8年时间,从一个仅有初中毕业文凭读过一年多职业高中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
两个月后,华罗庚胞姐华莲青和妻子吴筱元,携着亲属6人辗转数月到达昆明。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货物奇缺,生活艰苦。他们一家本住在离联大较近的青云街,因为日军飞机常来骚扰,就迁到昆明大西门外名叫黄土坡的小村子里。1980年5月21日,他在母校江苏省金坛县中学对全校师生作题为《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的谈话中回忆当年在昆明的日子时说:
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的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走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那个时候日寇封锁我们,国外的资料,甚至是杂志之类的都看不到。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还被迫去做买卖了。我住在昆明乡下,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
妻子吴筱元为了使华罗庚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研究,担负起了全部家务。她精打细算安排全家的衣食起居,为了省钱,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全家人的衣服鞋帽都是自己动手缝制,有时还为商店绣些花手巾,挣些零钱补贴家用。忙完家务夜深人静,她还主动帮丈夫誊抄文稿。
1939年9月28日,日军大肆轰炸昆明。黄土坡在昆明大西门外,离村不远的山谷里挖有许多作防空用的山洞,一个洞有半人高,可以蹲几个人。空袭时,华罗庚正在防空洞里给学生上课,一枚炸弹落在他们防空洞附近,黄土飞溅,连大树都被炸倒一大片,防空洞倒塌了,洞口被炸翻的土湮没了,他们被活埋在洞里。幸亏有师生冒险抢救,但又不能用铁锹,只能用手扒,好不容易挖出个可以喘气的小洞口,再继续把人扒出来。华罗庚被救出来了,但眼镜不见了,身穿的长衫下摆被扯断,变成了半截,脸面和手脚都破了,耳朵也被震出了血。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和教师们只得迁到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华罗庚住在大塘子村,往返学校要翻几个山头。因有腿疾行走不便,他只得坐农夫驾驭的两轮牛车来回赶路,因道路崎岖,人被颠簸得腰酸背疼。
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既从事教学又进行研究工作。此时,他的关于三角和的积分平均估计这一研究成果,成为处理低次华林问题的重要工具,国际上称为“华氏不等式”。他还跨进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领域。
1940年,华罗庚在生活条件异常艰难的环境里,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重要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全书共分十二章,除西格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外,全书所有定理的证明均包含在书中。他满怀信心地将手稿寄给中央研究院请求出版。
华罗庚盼望《堆垒素数论》尽早出版,但稿本交出去一年多了没有说法。多次去信查询,对方皆不予回答。1941年冬,校长梅贻琦亲自致函中央研究院依然杳无音讯。最后只得到了几句由他人转来的致歉语。
教育部无人能够评审华罗庚的这部著作。幸有二十世纪初叶著名数学家何鲁,他冒着灼人的炎热,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不时击案叫绝。何鲁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他阅后为该书作了长序介绍,并以政府当局仅有的六名部聘教授之一的“部聘教授”的声望,与熊庆来等一起坚持希望政府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1942年6月,华罗庚和许宝騄荣获“新中国数学会”第一届学术研究及著作发明国家奖励金,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获一等奖,许宝騄的数理统计论文获二等奖。
从内忧外患苦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怀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华罗庚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还希望能为国家的强盛和科学的发展大展雄图。
1944年7月初,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发动在云南大学“汇泽堂”举行抗日战争七周年时事报告会,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在昆明首次举行公开的大规模的讨论政治的集会。它有利于把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推向新高潮,因而国民党当局派人到会场捣乱。云南大学训导长宣布会议只谈学术问题,不准涉及政治,还叫熊庆来在大会上作大谈关于数学和读书的冗长发言。闻一多挺身严词驳斥,感染了全场群众。事后,中共组织派常与华罗庚联系的金坛同乡钱闻请华罗庚出面向熊庆来作解释,说服争取熊庆来。熊庆来告诉华罗庚说:“是训导长叫我去讲的,我上当了。”
国民党军政部次长、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经人介绍结识了华罗庚。一次,他对华罗庚说:“我有一道难解答的数学题目,请教过外国许多专家都无答复。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饭后将这道难题交给你带回去,如果数月后能得出计算结果,我就感谢万分了。”当晚,华罗庚将这个“难题”携回,第二天早上,他从卫生间出来,已将答案写在了一张手纸上。俞大维见答案切题、简洁而又圆满,怎么也没想到如此迅速,对华罗庚佩服之至。
半个多世纪后,华罗庚长子华俊东在美国时听说,当年俞大维请华罗庚解答的那道难题,是破译了一个日军的密电码。据说1941年初冬,中国获得一份日本军事情报,无人看得懂,报告了美国,但美国没有重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才惊悟,特地派人来华了解。也有文章说这个密电码问题是美国截获的日军偷袭昆明的密电码。华罗庚本人曾说,这个密电码就是梅比乌斯(A.F.Mobius)反转公式的应用。是用某种梅比乌斯公式将用整数表示的明码转换成用整数表示的密码,只要再用梅比乌斯逆变换就可以将密码转换成明码了。华罗庚的智慧在于能在一夜之间就洞察出这个联系。
有段时间昆明的警报减少了,华罗庚又把家搬到昆明城郊的西南联大租借的平房里。在这瓦檐低矮、潮湿拥挤的老屋里,他继续从事群论和矩阵几何研究,还与西革尔分别系统地研究典型域,证明了典型域的很多基本几何性质。由他创始的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正式诞生。他在昆明期间所进行的数学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真正的奇迹”。
1945年9月,中国人民坚持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结束。
12月1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的爱国师生,因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而举行罢课,遭到大批特务的殴打和追捕,军警向学生投掷手榴弹,炸死师生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那天华罗庚身在重庆,时已转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要求他赶回昆明,尽快了解和报告12月1日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
华罗庚回到昆明,随即各处走访,掌握了惨案发生前后的许多实情,及时向朱家骅作了报告。他据实报告,以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客观详细地记述了所了解的事件经过,并严正指责“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为失当”,“甚使志士心灰意冷”。
1946年春,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苏联访问,前后共三个月。回到西南联大后,闻一多与其他人一起筹组了欢迎会。由于听众太多,临时由屋内改到大操场演讲。会后,闻一多夸奖他“对苏联的情况介绍得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事后,华罗庚撰写了《访苏三月记》,在《时与文》杂志上分4期刊登,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向往,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6月底,全面内战的阴云笼罩大地,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开办了8年的西南联大宣布解散,在昆明孜孜矻矻8年的华罗庚也离开了。
9月初,华罗庚在庐山牯岭胡金芳饭店接受《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的专访。赵浩生问:“中国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同外国人比较如何?”华罗庚从座位上站起来,划了一个手势说:“绝对不比外国人差!” 赵浩生接着问:“科学与政治究竟能不能分开?”华罗庚左手托了一下眼镜,诚恳地回答说:“科学与政治实在无法分开……”他沉思良久,然后坦言道:“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决不是太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待着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
这些话真切地表达了以身许国、发展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赵浩生在采访后写道: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字,因为有这个名字,我们的国家才没有在国际理论科学界中被人遗忘;因为有这个名字,在一片荒芜的中国理论科学界中,才存在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