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期●散文●
寒松化名参军的难忘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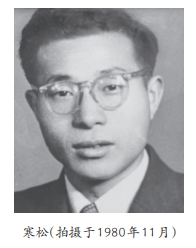

家国情怀,从家庭继承革命基因
我原名俞福敏,1930年11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我的父亲俞国庆,1891年生,原籍南汇县杜行乡东范行村(今属闵行区),因家贫仅读一年私塾便当学徒,饱受欺凌,成年后在纸厂、纱厂谋生,亲历辛亥革命失败与军阀混战。1927年,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起义中,工人们用空火油箱燃放鞭炮模拟机枪声,成功震慑军阀孙传芳部队。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遭到血腥镇压。父亲因家庭羁绊未能南下革命,转而进入上海中央银行工作。
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寇侵占上海,汪伪政权接管租界银行。父亲不愿为伪政府效力,转投私营小银行,收入锐减,家庭陷入困境。我二哥俞益敏初中毕业时,幸而获得《新闻报》奖学金,进入专科学校机械科深造。我则因市区学费高昂,回乡下杜行小学就读六年级。
这段经历意外成为我思想觉醒的起点。
校园觉醒,先进思想的转折点
在杜行小学,赵锋心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他经常与我谈心,从时事到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的小说,还推荐我读苏联名著和巴金作品。后来才知道,赵老师是共产党员,也是该地区地下党负责人。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该校学费较低,适合我家经济状况。中学期间,一位英语老师每次上课都会花十分钟讲时事,并指定课外阅读材料。这些经历让我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深刻了解。我三哥思想进步,常将新四军寄来的宣传资料交给我看,资料中的内容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5年,二哥机械科毕业。他提出想去敌后参加新四军,得到父亲支持后,询问我是否同行,我欣然答应。随后,我们找到赵锋心老师,他建议通过一条交通线直达根据地,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二哥去上海红十字医院药房找朱女士。于是,我和二哥分别化名为寒流和寒松。
临行前,母亲为我们赶制服装,用乡下织的土布做成衣衫裤子。此情景被二哥拍下照片,我在照片背后抄下唐人孟郊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革命征程,生死考验与信仰淬炼
这年6月,在上海红十字医院朱女士帮助下,我们踏上征程。朱女士告知还有几位青年也打算奔赴根据地,并指定二哥担任组长带队前行。约定见面那天,我们见到了陈永泰、张伟华和任某。大家商定次日上午集合,午饭后乘火车前往镇江,再渡江抵达瓜洲。
火车抵达镇江已是深夜,我们住进旅店。第二天发现船票只有次日早上的,于是在镇江停留一天,在金山风景区休息。次日一早,我们乘渡船到达江北的瓜洲。按照介绍信地址,我们找到一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挑起行李,叮嘱我们紧随其后。
路上,我们每人买顶草帽,对外宣称是同学游玩。走到渡口时,见岸边停着一条船,快到对岸时,炮楼上的伪军要求停船。交通员喊道:“快跳上岸。”我们四人跳到岸上。他又提醒:“不要奔跑,要快步走。”穿过树林来到公路,桥上有伪军注视着我们,我们默不作声,沿着小路前行。路边墙上写着“打倒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我们高兴地唱起救亡歌曲。
次日大雨后接到通知,敌人可能“扫荡”,要我们尽快离开。向导带我们前往汊涧镇的一户商人家里。到达镇口时,眼前一片汪洋,我滑入稻田,水深及腰。继续前行时,听到如雷鸣般的吼声,原来前面是河谷。河水漫过桥面,冲向下游。
向导拿起部分行李向前走,提醒大家站稳脚跟。二哥帮忙拿着行李,张伟华随即跟了过去。陈永泰手持扁担抢先走上前去,却一脚踏空被洪水冲走。二哥跳下河营救,但水势太猛,无法拉住他。最后,陈永泰被冲走。
二哥从行李中拿出绳子,一头拿在手里,另一头抛给我,让我扎在腰间。我拉着绳子向桥上走去,洪水把我冲得漂了起来,我干脆半躺着游过河去。我们继续前行,到达第二个联络站。次日清晨,房东主人通知我们在20多公里外的河滩边发现一具尸体,我们赶到那里,拉开芦席后,只见尸体肿胀,头发沾泥,双眼突出,根本认不出是谁。后来从皮夹带和穿的一双布鞋,才辨认出是陈永泰。
房东大爷帮忙购买棺材寻找坟地,将陈永泰安葬。我们在坟前举行告别仪式。回来后,由房东父亲陪同,我们一起到达新四军卫生部驻地——天长县姚庄。二哥把朱女士给的两封介绍信交给总务科长袁照和门诊部主任朱灵,我们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到招待所休息。房东父亲由新四军结算食宿费用及丧葬费用后离开。
朱女士还给了我们一封信,是交给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我们请袁科长转交,不久接到通知,宫部长要接见我们。宫部长客气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请我们吃午饭,让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工作安排事宜。
这里是新四军二师地区,距离姚庄五里地的大王庄是二师军工部工务科驻地。得知二哥是机械专科毕业,上级就把我们三人送到科长吴运铎的二师军工部工务科。二哥立即投入工作。张伟华学过两年机械,也被留下。一次,吴科长对我说,工厂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爆炸,建议我去学无线电技术。我与二哥商量后,同意去学习无线电。
吴运铎科长亲自陪我去大同镇电讯队驻地,见到了机务主任曹维廉。曹维廉用上海话和我交谈,问了几个数学方面的问题,并突然用英语提问,我都一一作答。最后,他对吴科长表示满意,说要把我从二师转到司令部三中队。自此,我便在新四军军部三中队电讯队学习无线电技术,直到上海解放后从部队调往上海市军管会,一直从事技术性工作。
从家庭启蒙到校园觉醒,再到革命征程中的生死考验,每一步都凝聚着信仰的力量。陈永泰的牺牲令人痛惜,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前行的决心。这段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更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缩影。※